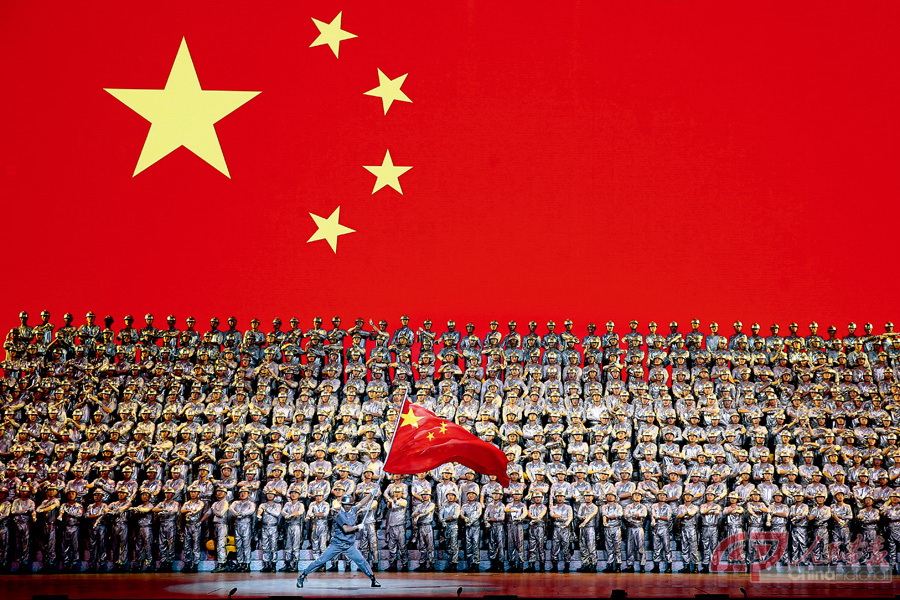马军,用行动描绘中国的“蓝天路线图”
发布时间 :2018-11-27 作者 :张劲文
中国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摄影/VCG
在中国环保界,“马军”这个名字几乎耳熟能详。他是中国环境保护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创始人,领导编写了中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2006年5月,他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人一同被列入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之中;2015年,他成为首位获得关注全球问题的“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的中国人。然而在我看来,比起想象中踌躇满志的成功者形象,他更像是一位谦逊的学者。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他曾在媒体单位供职,说起来还是我的前辈。在他的娓娓讲述中,我听到了一位环保斗士“三易其志”的成长故事,也看到了中国数十年来推动大气污染治理的历程。
从新闻记者到环保斗士
马军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在大学期间,他主修国际新闻专业。在图书馆的卷帙浩繁中,他十分喜爱读类似《国家地理杂志》的外文期刊。书中那些壮丽的自然遗产和神奇的物种,总能激发起他的好奇心与求知欲。“那个时候刚刚从封闭的年代走向开放,很少有人像现在的‘驴友’那样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所以书中的那些景象着实令我着迷。”
1993年,马军毕业后进入了香港的《南华早报》工作。媒体的工作性质让他有了更多接近大自然的机会。在外出采访中,马军留意着他走过的山山水水。然而,在他心底一直有一种违和感,就是眼前所见与书中记录的景象总是存在反差。他还记得,有一次去山西省采访,他穿越了汾河谷地,却只看到这条中国的“母亲河”最长支流干涸的河床。后来又下了雨,他看到,在烟尘迷蒙的雨天中,从周围的村镇流出来了五颜六色的污水,那里面掺杂了铜绿、铁锈。后来再去黄河流域的其他地方采访,他发现过去那些年,黄河上游的森林湿地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干流开始频繁出现断流。这些景象让他感到了一种危机。1999年,他在采访的基础上,经过总结分析,写成了《中国水危机》一书。“我一开始只是想把自己的所见、所感写下来,让大家都知道。后来渐渐发现,我更喜欢做这项工作,也觉得更有必要去做好。我那时从事的媒体行业在发现问题方面是强项,但是要研究解决问题就很不专业了,我需要更投入地去做好环境保护这件事。”恰好在当时,有一家国际环境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他就在2001年时进入了这家公司。在这里,他开始着手做环境调研评估,以及为客户研究梳理中国的环保法规,还协助客户开发了第一个供应链环境管理体系。
然而比起成就,马军看到的更多是挑战。他感觉到,仅仅有自己的努力是无法改变当前的环境危机的。虽然中国在1979年便颁布了《环境保护法》,之后还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制定了排污收费制度,并引入了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排污权交易制度,但是环保方面的执法并不严格。在各地方都在努力吸引外资的情况下,或多或少地缺乏治理污染的动力。马军认识到,必须要有广泛的公众参与,才能推动解决中国的环保问题。
2004年,马军入选美国耶鲁大学“世界学人”项目,前往耶鲁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访问学习。在那时,他系统地研究了西方的环境治理,做了中国与西方环境管理的对比性研究,期望能为中国找到可以借鉴的环境治理经验。
他所找到的经验,就是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公众参与。带着这个想法,马军回到了国内,并在2006年发起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这一次,他心无旁骛,一做就是12年。
2006年12月9日,“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因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发布“中国水污染地图”而入选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摄影/VCG
识别PM2.5,掀开中国大气污染治理新篇章
在发起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后,马军选择了他熟悉的水污染领域作为切入点,编写了“中国水污染地图”。与此同时,他通过数据的收集与研究,发现空气污染也是相当严重。虽然早在1982年,中国便制定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并在1987年通过了《大气污染防治法》,但是污染物监测种类与污染信息的发布力度都远远不及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最先开放的珠三角地区,以PM2.5浓度所代表的大气细颗粒物污染已经取代了早期以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10粗颗粒物为代表的一次污染。后来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和城市化加速,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的灰霾天数也日益频繁。但那时,中国城市空气监测指标仍然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没有将PM2.5、臭氧、挥发性有机物纳入其中。于是,马军便开始着手研究大气污染物监测的合理范围与信息公开的频次。
2009年,马军带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开展合作,开发了一个名为“空气质量信息公开指数(AQTI)”的数据。2010年,这两家机构联合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中国城市空气质量信息发布亟待完善》。在报告中,研究人员选取了中国20个城市和10个国际城市进行对比性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的空气污染程度基本是西方城市的3倍,但是污染信息公开程度还不及别人的1/3。马军说:“通过这个研究,我们认为中国法规是需要完善的,最主要的就是要将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纳入监测发布范围,而且在信息发布频次方面,仅有日均值是不够的,我们期望能实现以小时为频次的发布。”
与此同时,中国逐渐开始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2008年,主管生态环境的国家环保总局升级为环境保护部。当年,环保部便下达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项目。在2010年底,环保部发布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的第一次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拟制定不具法律效力的PM2.5参考限值,但不列入常规监测和发布范围。2010年11月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对此作出的解释是:“目前中国未展开对PM2.5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工作,缺少监测基础。因此,从全国角度制定实施PM2.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仍然较早。”
这引发了一次公众对于PM2.5的大讨论。2011年9月至12月,中国中东部地区发生了十余次较大范围的雾霾天气。连续的灰霾对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影响,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道。但环保部门发布的监测数据却常常依据2000年版的空气质量标准将其描述为“轻微污染”,这与公众的切身感受出现了巨大落差。
2011年前后也正值中国网络社交媒体的活跃之年。这一年,一些知名微博博主开始每天转发美国使馆实时发布的PM2.5信息,一些摄影师开始把每天固定地点拍摄的CBD街景图发到网上。北京更多的公众、环保组织和媒体开始关注PM2.5数值变动,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和个人甚至走上街头,主动去监测PM2.5数据。
马军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以长时间的系统研究来作为参与讨论的依据,得到了各方的关注。当讨论进行到2011年底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最终作出决定:PM2.5是涉及公众健康的,所以公众有知情权,而且PM2.5必须马上开始监测和发布。于是,《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重新修订,将PM2.5、臭氧纳入了监测范围,发布频次也改为每小时一发布,并定于2013年开始实行,这些都达到了马军和他的团队的期待。
2013年1月份,中国74个城市开始公布PM2.5监测数据,那时正好又赶上雾霾多发的时候。马军还记得仅有30分钟的《新闻联播》史无前例地用了10分钟普及PM2.5的相关知识。回想到这里,他十分欣慰地说:“PM2.5的监测和发布,对于保护中国公民的健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生活在北京,有切身的感受知道细颗粒物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他还记得,在标准修订之前,他曾数次前往孩子的学校进行交涉,要求取消在雾霾天气的长跑和出操,但都因苦于没有依据而作罢。但是到了2013年之后,有一天他的孩子告诉他:“如果AQI超过200,我要是再去操场踢足球的话就会被处分。”当听到这句话时,马军坦言,他的心里一下子放松许多。“因为我知道在污染最重的天气中,孩子们并没有直接暴露在伤害之下。”
2011年12月15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名为《蓝天路线图中国大气污染源定位报告》,研究人员发现电力、水泥、化工、钢铁等行业是废气排放最为集中的行业。摄影/东方IC
见证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完善
“中国大气污染治理最明显的成就都是在近5年取得的。”马军如是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一论断下,中国政府开始对环境治理模式进行高强度整改。2013年,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国十条”)公布,纳入了许多难以想象的措施。“比方说,国十条提出要控制燃煤的增长,要转变能源结构。2000到2012年,中国的燃煤总量增长了两倍,不仅排放了大量的燃煤废气,而且燃煤所带动的高耗能工业又产生了许多工业废气,成为了中国大气污染最主要的源头。”
中国对于大气污染的治理的重视也转变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态度。马军说:“中国在参与国际环境治理的态度有过一次很大的转变,追溯起来的话,那场关于PM2.5的讨论也是某种原因。”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代表与西方进行了激烈争论,强调的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不能为西方发展150年的后果埋单。但那时,中国燃煤已经接近世界的一半,按照预测,可能还要再翻一番才能达到排放峰值,这对于中国国民和世界都是不可承受的。“基于这样的认识,还有保护中国国民健康的想法,相信中国政策的制定者也释然了。减排不仅仅是环保和发展权的问题,更是保护本国国民生命健康权的问题。”于是,可以看到,中国燃煤的高速增长的势头在2013年戛然而止,之后进入了平稳和缓慢下降期。“有了这些政策,我们在与外国在推进气候治理方面更容易达成共识,也正是因此,才有了2014年习主席与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为2015年《巴黎协议》的达成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几乎与此同时,马军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始发布新的系列报告《蓝天路线图》。在马军看来,找回蓝天不会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认为第一步是需要监测和发布,这是基础,能让公众知情,让政策制定有依据;第二步就是预警和应急,在这期间,重污染天气还会频发;第三步是识别污染源头;第四步就是确定优先减排方向。我们之后每年都按照这个框架去评价中国在大气污染方面的治理成就。”
在马军看来,第一步已经基本落实。2013年,中国有74个城市实施了空气环境质量实时监测与公开,2014年,增加到190多个城市;2015年,这一成果覆盖到中国所有334个地级城市。“我们的大气污染监测工作,从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到超越他们,仅用了3年的时间。”。
同时,马军和环保界的同事们开始推动污染源的全面公开。在新《环保法》的修订过程中,中国政府广泛征求的环保界的意见。经过四次征求意见最终于2014年公布的新《环保法》中,纳入了马军和他的同事们的意见。“新《环保法》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成就是,专门将‘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开辟出一个章节,要求每个城市都要列出重点排污单位名录。”2015年,新《大气污染防治法》通过,也要求“在这些重点排污名录上的企业都要安装实时监测装备,并实时向社会公开监测数据”。
2014年,马军和公共环境研究院开发出一个手机APP“蔚蓝地图”,这里集成了来自中国各部门发布的污染源信息的数据,据他介绍已经有300万的下载量。经过数次更新换代,“蔚蓝地图”有了许多新的功能。点开APP,能看到遍布在中国大地上密密麻麻的数据,还有不少是红色或者黑色表示“超标”的数据。“看到这个,我们能很直观地看到中国在环境治理方面面临的重大挑战,但是这些数据也证实了中国环境治理信息公开所取得的成就。”
马军说,在“蔚蓝地图”刚上线的时候,中国各级环保部门也在建立自己的官方微博。每当公众举报时,常常用“蔚蓝地图”的截图去联系当地环保部门的微博,之后环保部门积极跟进,解决了不少问题,形成了良性循环。他还记得,当初作为一个环保组织的代表去跟某家上市能源企业交涉排污治理问题时,对方以“这个问题不重要”为由拒绝回应。没想到之后,许多公众拿着“蔚蓝地图”的记录去举报,再加上当地环保组织的积极活动,这家企业最后被要求整改,拆除了三个竖炉。马军回忆说:“关闭后,他们提交了一个减排报表,显示每年减排二氧化硫2600吨、烟尘405吨。PM2.5主要就是来源于烟尘。405吨烟尘,就意味着有405万亿微克PM2.5,这要是分摊到济南,乃至京津冀周边地区,是不可想象的污染。可以说,这是一次非常大的减排量。”
现在,马军正在研究新的项目——“蔚蓝生态链”。在他的设想中,所有关注环境的各方将被“链接”到一起,大企业将有效地推动和监督供应商进行绿色生产。谈到未来,马军说:“我们面临的问题很严峻,但是我依然抱有信心。随着环境信息不断公开化,我看到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许多个人也在积极关注和行动,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环保机构前行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