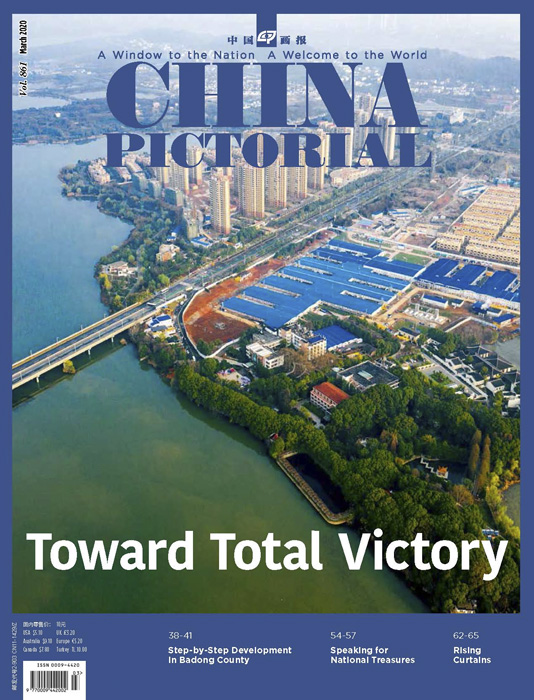1949年10月1日,翻译家冯亦代和他的新同事们,有说有笑,从北京宣武门国会街26号步行到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荣光,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无限憧憬。
新生活,是国家的,是民族的,也是每个人的。就在开国大典的同一天,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成立,乔冠华任局长,刘尊棋任副局长,冯亦代任秘书长。戴望舒来了,萧乾来了,杨宪益来了,爱泼斯坦来了,沙博理来了,魏璐诗来了……皆是一时俊彦,译遍华夏古今。新中国的对外出版发行事业,就此开启。
时间不曾止歇,70年倏忽而逝。
从当年的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到今天的中国外文局,从昔日的国会街26号到如今的百万庄大街24号,时钟的指针一格格划过,《人民中国》杂志社、《人民画报》社、《北京周报》社、《中国文学》杂志社、外文出版社、中国网,一个个鼎鼎大名的机构在这里挂牌,《毛泽东选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孙子兵法》《本草纲目》《红楼梦》,一本本讲述中国故事的多语种著作从这里走向世界。
国家的使者
1949年初,诗人戴望舒从香港回到内地。几个月后,他暂停了诗歌创作,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刚刚组建的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组。设施短缺,他就拿出自己的词典、打印机。人员不足,他就四处托人延揽人才。那时,翻译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是最紧迫的任务。身患严重哮喘病的戴望舒,为了节省时间,学会了自己注射麻黄素缓解病情。
不久之后,印着“外文出版社”字样的法文版《论人民民主专政》终于与英文版、印尼文版同时问世,《人民政协文献》的英、法、俄文版也出版了。
凝心聚力,翻译《论人民民主专政》,仅用了数月之功。精雕细琢,英译《毛泽东诗词》,则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中国文学》杂志英文版刊发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始自1958年。60年代初,一个由乔冠华、钱锺书和《中国文学》副总编辑叶君健等人组成的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成立了,目标是出版单行本。后来,赵朴初也加入进来,并请英文专家苏尔·艾德勒协助润色译文。经过“文革”数年延宕之后,小组成员还带着译文亲自到上海、南京、长沙、广州等地开讨论会,逐词、逐句反复斟酌。
多年以后,叶君健还清晰记得,《毛泽东诗词》英译本最终出版的日子,是1976年的“五一”。此时,距最初刊发毛泽东诗词英译,已过了18年。
翻译出版领袖著作、党政文献,这是70年来中国外文局始终肩负的光荣使命。
2014年10月8日,法兰克福书展开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这个世界最大的书展上首次亮相。这意味着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的这部图书,正式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语种向全球出版发行。
在中国外文局,翻译出版图书有一套标准的流程:先是翻译人员把中文转译成外文,再由外国专家改稿润色,定稿专家把关,然后才经过三审三校,最终付梓。
“我们在翻译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的过程中,为了保证译文准确、体例统一,除了一般的流程,后期还进行了十几遍的通读、校对。”外文出版社英文部副主任、一级翻译刘奎娟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不仅编校严谨,而且组建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定稿人团队,在这个团队里,既有中国外文局的王明杰、徐明强、黄友义等资深专家,也有来自外交部、中央编译局的权威人士。
英文如此,其他文种同样如此。据统计,截至2019年7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经出版了28个语种32个版本,海外发行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际社会读懂中国的权威读本。
文化的知音
1952年,虽然几家单位都向翻译家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戴乃迭伸出了橄榄枝,但还是刘尊棋的计划打动了他们。
“他早就有系统地把中国文学全部主要作品都翻译成英文的设想。他要我来主持这一计划。我将以‘专家’的身份决定该翻译、出版哪些作品,我还可以挑选一些书留给自己来翻译,乃迭和其他年轻的编辑、翻译可以帮助我完成这一任务。我很喜欢把未来很多岁月都用于这类工作的想法。”在自传中,杨宪益这样回忆。
杨宪益夫妇随即收拾行囊,卖了房子,举家从南京迁往北京。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翻译人生中,杨宪益与戴乃迭合作,把《楚辞》《关汉卿杂剧》《红楼梦》《老残游记》《鲁迅选集》等从先秦到现当代的百余种中国文学名著译成了英文。
20世纪80年代,一套名为“熊猫丛书”的中国文学译作在海外传播开来。每本书的封面上,都有一只憨态可掬的熊猫形象——它象征着中国。在这只熊猫的陪伴下,老舍、沈从文、汪曾祺、张洁、王安忆、王蒙等中国作家的作品走上了外国读者的书桌。
“考虑到在西方国家里,平装本‘企鹅丛书’非常普及,我就决定出版一整套由我自己来决定取舍的‘熊猫丛书’。这套纸面本丛书在20世纪80年代出了好几十种,非常畅销,并被转译成几种其他文字,包括法文和几种亚洲文字。”这个创意,又是杨宪益的手笔。
不只杨宪益,70年来,中国外文局还培养了唐笙、林戊荪等多位致力于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的翻译家。不只是“熊猫丛书”,70年来,中国外文局翻译出版中华文化典籍的脚步一直在前进。
1994年,《大中华文库》正式启动。这个以中国外文局为主,全国30家出版机构共同参与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
1997年,中国学者杨新、聂崇正、朗绍君与美国学者班宗华、高居翰、巫鸿共同撰写的《中国绘画三千年》问世。这是中国外文局与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的第一种。随后的几年间,中国学者徐苹芳、美国学者张光直等共同撰写的《中国文明的形成》等多部图书陆续出版。一种前所未有的合作出版模式从此创立:两国学者一起讨论写作提纲,实地观摩,分头撰写,交换阅读,提出修改建议,出版社最后定稿出版。
曾有人问,为什么两国出版人为了这套书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时任耶鲁大学出版社社长的莱登回答说:“为了我的孙辈们。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们能达到并珍惜美中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翻译不仅仅是从一种文字转换成另一种文字,更重要的是文字背后的文化习俗、思想内涵,因为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都有差别。”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相互理解,这也是杨宪益从事翻译事业的初衷。
共执译笔
1951年的一天上午,人民中国杂志社肃静的小院里,突然传出一阵笑声,还伴着英语交谈。
一对外国夫妇走进了办公室,让林戊荪印象深刻的是,女的高大,男的矮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是爱泼斯坦和他的夫人邱茉莉。
爱泼斯坦出生于波兰,担任过美国合众国际社的驻华记者。此时,他受宋庆龄之邀,来到北京参与创办《中国建设》杂志英文版,平时,也抽出一部分时间到《人民中国》编辑部改稿。彼此熟悉后,大家都叫他艾培。
“那时我和许多同志都很年轻,也都是新手,而他是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大家共同的感觉是,他知识渊博、见多识广、和蔼可亲、乐于助人。”林戊荪说,爱泼斯坦不仅改稿又快又好,而且经常对外宣工作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记得有一次,他对我们的一些特写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新闻特写在细节上必须绝对真实,不能有任何的虚构。这类及时的提示,使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深受启发。”
这样的教益,20多年后的黄友义也领受过。
“我1975年到外文出版社工作时,艾培正在英文部当改稿专家。这让我有机会得到艾培手把手的指导。我参加工作翻译的第一篇稿件,就交给他修改润色。等我拿回来时发现,我用老式打字机打印出来的稿件每一页都被他用红笔画成了‘大花脸’。”有些字迹黄友义辨认不出来,就到他的办公桌前请教,“他对一个年轻人的打扰丝毫不反感,反而仔细解释他为什么这么修改。”
爱泼斯坦、沙博理、陈必弟、魏璐诗、华依兰、史克、土肥种子……自1949年至今,中国外文局聘请外国专家2000人次,是新中国聘请外国文教专家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机构。
4年前,年过花甲的菊池秀治来到中国外文局,成为众多外国专家中的一员。虽然有着30多年的翻译经验,但面对一部部译稿,他仍然一丝不苟。办公桌上的一本日文词典,因为经常查阅,已经有些破旧了。拿起一本刚出版不久的《中国速度: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纪实》日文版,翻到版权页,上面清晰地印着“日文改稿:菊池秀治”,举手投足间,满是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更透露出他对中国的一片深情。
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说明中国,需要中国人的奉献,也离不开这些外国专家的智慧。
70年时光流转,时间指向新时代。戴望舒们、杨宪益们、爱泼斯坦们的故事告一段落,黄友义们、刘奎娟们、菊池秀治们的故事仍在继续。“读懂中国”丛书,正在向世界说明“中国从哪里来、中国走向何方”;“如何看中国”丛书、“辉煌中国”“大美中国”“人民中国”系列丛书,展现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丝路百城传”丛书,描绘出“一带一路”沿线上100余座中外城市的性格……如今的中国外文局,已在1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6家驻外机构,与全球30个国家的出版机构合作共建50余家“中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与波兰、秘鲁、泰国等国合作共建10个中国图书中心,每年以40余种文字出版近5000种图书、以13个文种编辑34种期刊,书刊发行遍布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时间在继续,翻译就会继续,出版就会继续,中国外文局的故事就会一直讲下去。